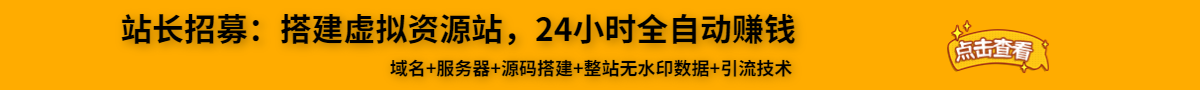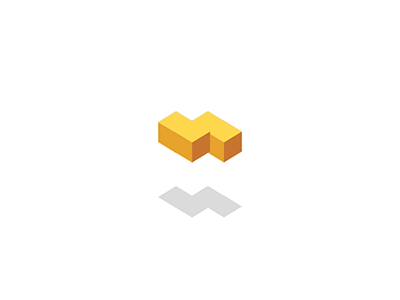死亡之花,如此娇羞
庄子是一个凡人,有人的七情六欲,也食人间烟火,所以说,在庄子妻死的时候,一开始也是很感“概”的,“概”通“慨”,情绪很激动。“慨”又假借为“嘅”,“嘅”是因悲伤而叹息。
毕竟妻子与庄子生活了多年,一起生儿育女,含辛茹苦,只共过苦,未同过甘,甚至好多回,穷得要死了,庄子曾借米度日,要靠钓个鱼打个鸟改善一下伙食。
庄子先“慨”后“歌”,从有情到无情,是因为庄子“通乎命”了,看破生死了,就不会为生死所左右,就不会有情感大变化了,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,这可以称为以理制情。
庄子由于通达了生命的真相,因此能够做到“安时而处顺,哀乐不能入也”,他自然而然也就“悬解”了,不再为生死所困了,真正地超脱生死了,然后才有了他留名千古 的“鼓盆而歌”。
庄子妻死,他鼓盆而歌,是违背人情世理的,因此受到了惠子的激愤批判。但庄子是一个不拘于世俗之礼的人,妻子死后,他“箕踞”于地,两腿伸直岔开,就像一个簸箕一样,这对于死者与亲朋而言,是极不礼貌的。况且,他在两腿之间还倒扣着一个破瓦盆,有一下没一下地敲着某种节奏,配合着庄子的生命感叹之歌。
这种生命之歌,能听懂的人太少了,唯一的朋友惠子也是置若罔闻,不知所云,相反,却曲解为庄子对新故爱妻的大不敬。本该“噭噭而哭”的他却“鼓盆而歌”,真是不可理喻。
在爱妻死亡面前,在世礼俗情面前,庄子的行为很叛逆,很另类,很不合人情,这是因为庄子的思想很超越,很前卫,很与众不同。
哭也好,歌也罢,都是渲泄情感的方式,面对生命的种种境遇,伴随我们的喜怒哀乐,我们如何保持一颗平常心,不为物喜,不为己悲,这就需要考量我们的智慧与定力了。
庄子之所以如此离经叛道,不为妻死而悲伤,无情于事,不拘于俗,其原因就在于洞察了生命的天理,看透了生死。因此,他歌颂着造化的奥妙,他歌叹着生命的神奇,直面生死,悠然而来,悠然而往,不带走一片云彩,何不潇洒歌一回呢?
生死只是生命的自然现象而已,也只是人的观念而已。气聚则生,气散则死,万物是相互转化的,生命也是轮回的。因此,破除对生的执迷留恋,对死的忧惧抗拒。
向庄子学习,学会道眼观世界,学会齐生死、善死生,达观面对死亡,才能坦然面对生命中的种种境遇。
生命存在的意义就在于对“形体”生命的突破与超越,拓展内在的精神生命,不为生死所囿,从而获得生命的真正超脱,防止“其形化,其心与之然”,心随形化,就是“心死”。
“哀莫大于心死,而人死亦次之”。心死,是人的精神生命的终结,人死是人的肉体生命的结束。没有灵魂生活的人生,只有安逸与享乐,爱因斯坦称之为猪栏的理想。《庄子》里有一个成语,薪尽火传,柴可以燃尽,但生命之火可以无尽地传递下去。也许只有得道了,以道为友,与道同游,我们的精神生命才会与日月齐寿,与天地同在。
庄妻死了,庄子鼓盆而歌,令人不解。庄子快要死了,听听他会说些什么,是不是真正超脱?
庄子将死,弟子欲厚葬之。庄子曰:“吾以天地为棺椁,以日月为连璧,星辰为珠玑,万物为(齐)送。吾葬具岂不备邪?何以如此!”弟子曰:“吾恐为鸟鸢之食夫子也。”庄子曰:“在上为鸟鸢食,在下为蝼蚁食,夺彼与此,何其偏也!”
庄子快要死了,弟子们想要厚葬他。
庄子说:“我用天地来做棺椁,用日月来做双璧,用星辰来做珠玑,用万物来做陪葬。这样,我的葬礼还不厚重完备吗?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吗!”
弟子说:“(按你说的那样),我们担心乌鸦老鹰等鸟把你吃了。”
庄子说:“在地上被乌鸦老鹰吃,在地下被蝼蚁吃,从乌鸦嘴里夺过来给蝼蚁吃,你们为什么这么偏心啊!”
庄子面对生死,一如既往地“黑幽默”,还是如此地超然洒脱。他的妻子死了,他很另类地“鼓盆而歌”,他自己快要死了,也能笑谈“厚葬”与否。
这一切都因为他已经超越了生死的困局,达到了“天地与我并生,万物与我为一”的至高境界。
庄子接着对弟子作了最后的“开示”。“以不平平,其平也不平;以不徵徵,其徵也不徵。明者唯为之使,神者徵之。夫明之不胜神也久矣,而愚者恃其所见入于人,其功外也,不亦悲乎!”
“如果以不公平的方式来对待公平,这种公平其实还是不公平;如果以不能验证的东西来作证明,这种证明还是不能算作证明。自以为是的聪明人总是被人役使,而得道的神人却顺其自然,返本守真。这种自我炫耀的聪明人早就不如素朴自然的神人了,而愚昧的人还在顽固地依恃于自己的偏见沉溺于世俗,但他的做法总是事与愿违,这不是很可悲吗?”
对待死亡,庄子的弟子们不仅仅有“偏心”,而且更有“偏见”。有偏心偏见,就是一个“愚者”,是一个自以为是的“明者”,而不是一个顺乎自然的“神者”。真正的神者,应该是一个脱离“偏见”远离“世俗”的人。
“生死”只是世人的一种观念而已,其实“方生方死,方死方生”,生死是一个东西,而不是两个分裂的东西。
庄子将“死亡”看作一个很自然的事情,对于他来说,是一个“喜剧”,而不是悲剧,从“郦姬哭嫁”这个故事可以清楚这一点。也算是“以不徵徵,其徵也不徵”,死亡的好与坏在我们有限的能力之内是不能证明的。庄子从大道的角度俯视人间百态,天地万物如此渺小,人类更是微不足道,如果再自以为是,争执不休,就更为可笑可悲了。